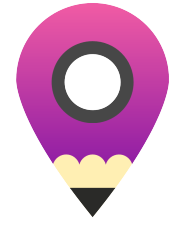供参考。
这个故事已经有5年多了。
旅行 Matthew Leifheit 的拼贴画
Matthew Leifheit 的拼贴画1983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就在我去曼谷拍电影之前不久,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被称为“比基尼杀手”的连环杀人犯,一个英俊、有魅力的临时宝石小偷,名叫查尔斯·索布拉吉,他已经手术了1970 年代初期的泰国。我的朋友认识一对福门特拉岛夫妇,他们通过中继从南亚走私海洛因,他们分别被引诱致死。他们是 Sobhraj 在所谓的嬉皮小径上扼杀的众多西方游客中的两个。这条路从欧洲延伸到南亚,由西方辍学者徒步跋涉,他们抽烟并与当地人联系。 Sobhraj 会用他们所有的钱来掠夺这些精神上口渴的流浪者,蔑视他认为他们松散的道德。
曼谷的生产延误使我在几周内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设备。这是一个迷失方向、臭气熏天、交通疯狂、可怕的城市,到处都是乞讨的僧侣、青少年团伙、摩托车、寺庙、凶残的皮条客、可怕的妓女、下流酒吧、脱衣舞会、街头小贩、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地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在发现 Captagon 是一种强效安非他明在柜台上出售后,我在租来的手动打字机前连续坐了 12 或 14 个小时,大量写诗、日记、故事和给朋友的信。这种药物有助于写作。在一次超速狂欢之后,我喝了 Mekhong,一种有毒的威士忌,据说含有 10% 的甲醛,据传会导致脑损伤。
在与自春节攻势以来一直住在泰国的英国和法国侨民的晚宴上,我听到了更多关于 Sobhraj 的谣言。他会说七种语言。他从五个国家的监狱越狱。他伪装成以色列学者、黎巴嫩纺织品商人以及其他一千种东西,同时以吸毒和抢劫犯的身份在南亚搜寻旅游受害者。几个小时后,他因喝酒结识的人在酒店房间或行驶中的火车上醒来,护照、现金、相机和其他贵重物品都不见了。
在曼谷,事情发生了严峻的转变。 Sobhraj 使自己成为他在希腊罗得岛遇到的一位加拿大医疗秘书的热情对象——一位名叫 Marie-Andrée Leclerc 的女士,她正在和她的未婚夫度假。勒克莱尔辞去了工作,甩了未婚夫,飞往曼谷加入索布拉吉。她一到,他就命令她根据需要摆出他的秘书或妻子的样子。 Sobhraj 很少操她,这让她很懊恼,而且只有当她的常识威胁到她华丽的浪漫幻想时才会这样做。
他们在乡下走来走去,给游客下药,把他们带到半昏迷状态,带到索布拉吉租来的备用公寓。他说服他们当地的医生都是危险的庸医,而他的妻子,一名注册护士,很快就会让他们恢复健康。有时他让他们病了好几个星期,勒克莱尔给他们服用一种由泻药、吐根和 Quaaludes 组成的“药酒”,让他们大便失禁、恶心、昏昏欲睡和困惑,而 Sobhraj 篡改他们的护照,用它们过境,花掉他们的现金,并将他们的贵重物品围起来。
1975 年,他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名叫 Ajay Chowdhury 的印度男孩。 Chowdhury 与 Leclerc 和 Sobhraj 一起搬进来,两人开始谋杀某些“客人”。与 Sobhraj 之前的任何罪行不同,“比基尼杀戮”尤其令人毛骨悚然。受害者被下药,被驱赶到偏远地区,然后用木板捶打,浇上汽油并活活烧死,在喉咙被切开之前被反复刺伤,或被半勒死并拖入海中,仍在呼吸。
Sobhraj 之前曾因意外服药过量而杀人。但比基尼杀戮是不同的。他们经过精心策划,一反常态地不优雅。它们发生在 1975 年至 1976 年之间一段奇怪的压缩时期,就像一阵持续数月然后神秘停止的愤怒。 Sobhraj 和 Chowdhury 在泰国、印度、尼泊尔和马来西亚屠杀了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至少八起,包括加德满都的两起焚烧杀人案和加尔各答的一起强行浴缸溺水案。
Sobhraj 最终于 1976 年在新德里被捕,他在 Vikram 旅馆的宴会上给一群法国工程专业的学生下药。他诱骗他们服用“抗痢疾胶囊”,许多人当场吞下,几分钟后病得很重。酒店前台服务员被 20 或更多人在餐厅里呕吐而感到震惊,于是报了警。完全是偶然的,出现在 Vikram 的警官是印度唯一能够从多年前在监狱医院进行的阑尾切除术留下的疤痕中可靠地识别出 Sobhraj 的警察。
在新德里因一系列罪行(包括谋杀)受审,索布拉杰只因较小的指控而被定罪——据推测,这足以确保他远离社会多年。在曼谷,因为速度而失眠,我开始怀疑 Sobhraj 并没有像报纸报道的那样真的被监禁在印度监狱中。我很偏执,以为我在想他,他也在想我。在我睡觉的极少数时间里,我梦见了他,想象着他穿着黑色紧身长袜的轻盈致命的身影,像 Irma Vep 一样爬进我大楼的通风管道和通风井里。

Charles Sobhraj 和 Marie-Andrée Leclerc 于 1986 年。照片由 REX USA 提供
1986 年,在监狱服刑 10 年后,Sobhraj 在狱友和他在外面集结的帮派的帮助下,从新德里的 Tihar 监狱中逃脱。他用掺杂水果、糕点和生日蛋糕的节日礼物给整个警卫室下药,从而逃脱了。 1976 年 Sobhraj 被捕时,印度与泰国没有引渡条约,印度同意在他在印度服役后遵守一项特别引渡令——一项有效期为 20 年的不可更新的命令。
泰国有六起一级谋杀的证据。比基尼杀戮事件毁了旅游业好几个季节,索布拉吉愚弄了曼谷警方。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他被引渡,他将在下飞机时被枪杀。
他从德里逃到果阿。他骑着一辆粉红色的摩托车在果阿周围嗡嗡作响,伪装成一系列荒谬的样子。最终,他在 O’Coqueiro 餐厅使用电话时被抓获。越狱的全部目的是被捕并因越狱而被给予更多的监禁时间——刚好超过泰国引渡令的有效期。
经过多年对 Sobhraj 的零星兴趣,我想见见他。所以在 1996 年我提出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旋转 .我并不是特别想写一篇文章,尤其不是为了美化版 虎扑 ,但他们愿意付钱,所以我去了。
我首先联系了理查德·内维尔,他在新德里接受审判时曾与 Sobhraj 相处了很多时间。内维尔写了一本书, 查尔斯·索布拉吉的生平与罪行 ,现在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偏远地区。他仍然做着关于索布拉吉的噩梦。 “你应该去满足你下流的好奇心,”他告诉我,“然后尽可能远离那个人——永远,永远不要再和他有任何关系。”
当我到达新德里时,索布拉吉的十年越狱刑期即将到期,引渡令也即将到期。我搬进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开的一家便宜的旅馆。我经常在康诺特广场的印度新闻俱乐部闲逛,那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最喜欢的地方。俱乐部类似于 1960 年左右的 Bowery 杂货店的大厅。用辣椒炸制的西班牙花生盘子是菜单上唯一可食用的项目,饮料免费提供。墙上挂着像神殿一样的记者肖像,他们在醉醺醺地离开新闻俱乐部后被车流碾过。
我的新同事充满了耸人听闻的 Sobhraj 轶事——关于他与被监禁的政客和实业家的友谊的故事,以及他被提供给他的故事的电影版权的巨额资金。一种 印度斯坦时报 记者向我保证,我永远不会进去见他。 Sobhraj 已被媒体隔离,当新的监狱长接任时,他曾经在 Tihar 监狱享有的奢侈特权也被切断了。
新的监狱长是印度执法界的传奇人物基兰·贝迪(Kiran Bedi)。作为前网球冠军,她成为了第一位印度女警察。她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而且矛盾的是,她是右翼印度人民党的狂热支持者。在一个腐败的警察队伍中,她狂热地清廉,曾多次被给予“惩罚职位”来劝阻她,但她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热情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命令国务部长们“下令”。例如,非法停放的汽车被拖走——她成为了她的老板无法摆脱的民族英雄。在贝迪到来之前,蒂哈尔曾被称为印度最糟糕的监狱,这说明了一些事情。贝迪将她的惩罚任务变成了另一场公关胜利,将蒂哈尔变成了一个康复场所,引入了早晨冥想、职业培训和瑜伽课程的僵化方案。
一天早上,我在监狱管理大厅里坐了几个小时,靠近一个装满没收武器的橱窗。无精打采的士兵经过,打着哈欠,抓着他们的球。一群兴奋的女士们到达了,一些穿着长裤套装,一些穿着纱丽,围着一个身材矮小,身材矮小,四肢雪白,留着短发,脸上攥着拳头。这是贝迪。根据新闻俱乐部朋友的建议,我告诉她我想为纽约杂志写一篇关于她的简介。在她面前只需要片刻就可以感受到她的自负和精明的巨大。
她说,欢迎我在监狱度过时光。但是,如果我打算与 Sobhraj 交谈,我可以忘记它。如果她让媒体和他说话,她会危及她的工作。不管这是否属实,我确信她打算成为现场唯一的名人。我问索布拉吉怎么样了。
“查尔斯变了!”她用像鸟一样的印度英语口音宣布。 '通过冥想!出狱后他将与特蕾莎修女一起工作!现在没人能看到他——他已经康复了!下一刻,她建议我在印度呆几个月。她说,如果我同意代笔写她的自传,我可以在那里过得很好。这看起来很奇怪。
我还没来得及呼吸,我就被挤到外面,挤进了一辆球形汽车,汽车沿着包围着蒂哈尔四个独立监狱的内围墙飞驰,这是一个拥有许多开放空间的巨大建筑群,就像一座小城市。我们到达了一个检阅台,在那里我被带到一排身着正装的贵宾的尽头。在我们下方,有2000名囚犯坐在莲花座上,许多人身上都涂满了彩色粉末。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做什么,穿着破牛仔裤和一件 Marc Bolan T 恤。贝迪的演讲是庆祝洒红节,这是一个鼓励爱、宽恕和欢笑的印度教宗教节日。和涂抹的彩色粉末。
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办公室。贝迪宣布她第二天将前往欧洲参加一个会议,为期数周。她的新传记作者我渴望获得 Tihar ashram 的全部效果,她在一些便条纸上草草写下了所有四个监狱的通行证。我在。有点。
三个星期以来,每天早上,我都乘坐出租车缓缓驶向 Tihar 监狱,穿过令人兴奋的人群和混乱的交通,绕过大象和灰烬,饥饿的奶牛。一切都在令人震惊的高温下闪闪发光。我们经过了红堡,空气中弥漫着油腻的黄色烟雾和汽油燃烧的黑烟。乞丐们蹲在路边的沼泽里,看着车流,偷偷拉屎。
我的通行证每天早上都在两扇巨大的铁门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安全缓冲区中接受检查——同样的检查也令人怀疑。每天,上级军官都给我指派了当天的看管人,我试图向最年轻的守卫妥协,他们最放松,最宽容,经常在他们闲逛抽烟和朋友聊天时抛弃我。
他们向我展示了蒂哈尔的任何我想看的东西——菜园;瑜伽课程;电脑课;被水仙花和芙蓉覆盖的湿婆神和毗湿奴神殿;铺有祈祷垫的宿舍牢房;围在织布机旁闲聊的女人散散开来;一家面包店里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赤脚男人,穿着像尿布一样的短裤,把面团铲进工业烤箱。我遇到了被控贩毒的尼日利亚人;克什米尔人被指控犯有恐怖爆炸;澳大利亚人被指控过失杀人;被指控在监狱中被折磨多年,仍在等待审判日期的人——印度的“未经审判的人”通常在他们被审判之前就已经为他们被指控的罪行服满刑期,如果他们被无罪释放,他们就不会得到任何审判。非法监禁的赔偿。
除了索布拉吉,我什么都看到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他在哪里。但一天下午,经过三周的一天探访后,我很幸运:我牙痛了。我的看护人带我去看监狱牙医,在一个小木屋里,外面排着大约 30 个人,等待伤寒疫苗接种。
我的监护人在与阳台上的护士交谈时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同时她将同一根针刺入一条又一条手臂。我问排队的人是否有人可以给 Sobhraj 留言,一个戴着发光串珠项链的尼日利亚人拿着我的笔记本飞快地跑了,在我预约完牙医后回来了。当他把一张折叠的纸塞进我橙子的口袋里时,我的脸被 Novocain 弄得麻木了 去创造 .
几个小时后,我打开了它,因为 3 号监狱的年轻监狱长骑着摩托车把我带回了我的旅馆。 Sobhraj 写了他的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并指示当天晚上给他打电话。在电话中,我被告知要在第二天早上九点整在他位于 Tis Hazari 法院的办公室与律师会面。
Tis Harazi 法院大楼是一个奇迹,从 William S. Burroughs 的眉毛中涌现出来。一个穿着栗色灰泥的利维坦,外面涌动着诉讼人、乞丐、卖水者和各种奇怪的人类形式的海洋。在大楼的一端,一辆翻倒的公共汽车,里里外外都被烧焦了,里面住着一大群凶残的猴子,他们兴奋地从分开的座位上扯下精益求精,尖叫着冲着路人扔粪便。一条浅沟将法院场地与用作律师事务所的蹲坑水泥地堡迷宫般的台地隔开。办公室。
律师是一个看上去毫无骨气的男人,年龄难以猜测,皮肤黝黑,有着雅利安人的特征。他让我把相机留在后面。我们走到法庭,穿过人群,爬上楼梯来到一间昏暗、四四方方的法庭。
我在一大群原告中认出了 Sobhraj,他一个人走近一位戴着亮黄色头巾的胆怯的锡克教法官的长凳,他若有所思地喝了一瓶可口可乐。律师介绍了我们。

1977 年 4 月,Sobhraj 被带到新德里的 Tihar 监狱。 摄影:REX USA
Sobhraj 比我预期的要短。他的椒盐色头发上戴着一顶运动型贝雷帽。蓝色细条纹白衬衫,深蓝色长裤,耐克运动鞋。轻微,尽管他增加的任何重量显然直接影响了他的屁股。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让他的眼睛显得又大又湿,那是一只多汁的海底哺乳动物的眼睛。他的脸暗示了一个有点摇摇欲坠的林荫大道演员,以前以他的美丽着称。它通过了“友好”表达的形态。
我避开他的眼睛,盯着他的嘴。在他肉质的嘴唇后面,他的下牙非常不规则,呈锯齿状,隐约暗示着一种掠食性两栖动物的嘴巴。我决定我在他嘴里读了太多东西,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鼻子上,这更令人愉快。
他正在等待为他一直发起的一些琐碎诉讼辩护,主要是为了出狱一天并在当地报纸上引起轰动。 “你需要在外面等”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律师会告诉你的。”他带我走到法院正面一扇高大的长方形窗户下的一个地方。
半小时后,Sobhraj 的脸出现在窗户里,被框在一个没有灯的牢房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问了我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在哪里上的大学,我写了什么样的书,我住在哪里,我会待多久印度,一个虚拟的尼亚加拉沙漠,它在追问我的政治态度、我的宗教信仰(如果有的话)、我最喜欢的音乐、我的性行为。我对一切都撒了谎。
“你住在新德里的什么地方?”他问我。我嘟囔了一些关于欧贝罗伊酒店的事情。 “啊哈,”索布拉吉厉声说。 “律师告诉我,你是从 Channa Market 的一家旅馆给他打电话的。”
'那是真的,但我要搬到欧贝罗伊。可能是今晚!'我语重心长的说道。我突然想到 Sobhraj 的一个仆从,其中总是有很多人在外面,突然拜访我,让我参与一些听起来很无辜的计划,让我在没有任何通行证的情况下入狱.
无处不在:“也许你可以和我一起为电影写我的人生故事。”当我告诉他我只会在印度呆几周时,那种感觉像桃核一样大小的东西突然堵住了我的喉咙。 '我的意思是以后。我出来之后。你可以回来。
当一位烦人、笨手笨脚的记者慢步走到窗边打断我时,我感到宽慰,尽管我每 15 分钟就贿赂 Sobhraj 的警卫以获得与他交谈的特权。
过了一会儿,Sobhraj 从拘留所出来,被他的手腕和脚踝铐住,并被锁在身后蹒跚而行的士兵身上。他在法院的远处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被允许走在他身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告诉我的,没有遭到他的卫兵的任何反对。我们走进一圈军队人员,冲锋枪指着我们俩。其他有法庭事务的囚犯只是与他们手无寸铁的护送手牵手走,但 Sobhraj 很特别。他是一个连环杀手,也是一个大名人。人们冲过消毒警戒线,乞求他的签名。
“现在,”我们边走边问他,“在基兰贝迪接管监狱之前,人们说你真的负责这个地方。”
“她有没有告诉你我正在写一本书?”他厉声喝道。 '关于她?'
'她提到了一些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是一个作家。喜欢你。在监狱里没有什么可做的。阅读,写作。我非常喜欢弗里德里希·尼采。
'哦是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
'对,就是这样。我有超人的哲学。他和我一样,对资产阶级道德毫无用处。索布拉吉弯下腰,锁链叮当作响,拉起一条裤腿。 “这就是我管理监狱的方式。你知道那些微型录音机吗?我会在这里把它们贴在自己身上,你看。在我的袖子下。我让看守谈论收受贿赂,把妓女带进监狱。
他给我看了他一直放在衬衫口袋里的橡皮泥钱包里揉成一团的一些文件。
“这些是奔驰的文件,我会在这里上交,”他指着办公室敞开的门说。 '它适用于我的保释金。当我离开蒂哈尔时,我必须给他们一些钱。
“休假,你的意思是——”
“当我离开去与特蕾莎修女一起工作时。”哎呀。
“我需要问你一件事,查尔斯,”我尽可能坚定地重复道。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这只是要点),我注意到 Sobhraj 把我之前告诉他的关于我自己的一切都做了一种精神拼贴,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反馈给我,并附有各种似是而非的修改,作为关于他自己的启示。这是反社会人士的标准技术。
“你也想要我的签名吗?”
“不,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在泰国谋杀了所有这些人。”
与我所希望的破坏效果相去甚远,Sobhraj 对一些私人玩笑笑了笑,开始用衬衫清洗眼镜。
“我从来没有谋杀过任何人。”
“斯蒂芬妮·帕里呢?维塔利·哈基姆?尼泊尔的那些孩子?在圣诞节假期期间,Sobhraj 和 Chowdhury 带着 Leclerc,抽出时间在加德满都焚烧了两名背包客。
“现在你在谈论吸毒者。”
“你没有杀了他们?”
“他们可能是……”他寻找合适的词。 “呃,被一个集团清算,因为交易海洛因。”
“你是辛迪加吗?”
'我是一个人。一个集团有很多人。
“但你已经告诉理查德·内维尔你杀了那些人。我不想冒犯你,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杀了他们。
'我刚刚告诉过你了。'我觉得时间在溜走。我认为再次见到这个人是不明智的,一旦他与梅赛德斯结束了这桩阴暗的交易,他们就会带他回蒂哈尔。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他在沉思着沉默后说道。他秘密地靠在我身上。其中一名警卫咳嗽了一声,提醒我们他的存在。 '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女孩。她喝醉了,Ajay 把她带到了 Kanit House。我们知道她,你看。我们知道她与海洛因有关。他接着讲述了他是如何杀死 Teresa Knowlton 的,Teresa Knowlton 是一位绝对没有接触过海洛因并计划成为一名修女的年轻女性,这或多或少与他在 25 年前向 Richard Neville 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完全一致。她的尸体是第一个被发现的,穿着比基尼,漂浮在芭堤雅海滩上。因此,比基尼杀手。
当他讲完一个又长又丑的故事时,我说:‘我对你如何杀死她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即使你为某个香港辛迪加工作,也一定有你而不是其他人会这样做的原因。
一名警卫表示 Sobhraj 可以进入办公室。他站起来,铁链发出巨大的叮当声。他拖着脚走了几步,从肩膀上往后看了看。
“这是个秘密,”他说,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然后他消失了,挥舞着梅赛德斯的头衔,伊阿古直到最后。

1997 年 4 月,Sobhraj 抵达巴黎后,在一家法国报纸上阅读有关他自己的信息。 REX USA 摄
我认为 Sobhraj 和 Chowdhury 一定是加快了速度。我经常推测比基尼杀人事件是由安非他明精神病引发的扭曲的同性恋死亡仪式。我想向孟买警方提出这个建议,但因为我自己在超速,我有一种偏执的想法,如果我提出来,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给我做药检。
我去见了 Madhukar Zende,一位令人印象深刻、性格古怪的猫科警察专员,他向我展示了索布拉吉的同伙手写的证词,用圆珠笔或铅笔潦草地写成,承认在白沙瓦、卡拉奇和克什米尔犯下了多起盗窃案,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交通的狂热。 Zende 曾两次逮捕 Sobhraj:一次是在 1971 年 Zende 42 岁生日时,一次是在新德里 Ashoka 酒店的珠宝盗窃之后,另一次是在 1986 年 Tihar 越狱之后。
他带着讽刺的感情谈到了 Sobhraj,回忆起 1970 年代初期,当时 Sobhraj 在马拉巴尔山(Malabar Hill)拥有一套公寓,并通过以惊人的折扣提供被盗的庞蒂亚克和阿尔法罗密欧,从而在宝莱坞赢得了人气,并竖起了他的 D’Artagnan 胡子。对于更狡猾的骗局,他在奥米斯顿路的果汁吧和跳蚤旅馆招募走狗,在泰姬陵或印度门附近的欧贝罗伊(Oberoi)对富有的游客进行吸毒和抢劫,以继续练习。
“他对女人和金钱很感兴趣,”曾德叹了口气。 “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心碎的痕迹。” 1971 年,Sobhraj 一直在果阿的 O’Coqueiro 餐厅等待国际电话,这时 Zende 伪装成游客将他逮捕。
我坐在 Sobhraj 被抓获的地方附近,小而呈虹彩的蜥蜴在 O’Coqueiro 鼠尾草绿色的墙壁上爬上爬下。这是果阿的淡季。侍者在餐厅里漫无目的地站着,就像空荡荡的舞厅里的舞男。
在阴暗的阳台上,业主吉内斯·维加斯 (Gines Viegas) 为我提供朗姆酒和可乐,同时他讲述了他在非洲和南美洲担任旅行社多年的故事。他是一只易怒的乌龟,但他时不时地插入索布拉吉每晚出现在餐厅使用电话的几周的新鲜细节。
“他打电话给他在法国的母亲,”维加斯告诉我。 '他每次看起来都不一样,戴着假发,脸上都化了妆。他用腻子把鼻子弄大了。当 Zende 在这里进行他著名的监视时,他穿着百慕大短裤和旅游衬衫。我马上就知道他是一名警察。
Madhukar Zende 现在已经死了。吉内斯·维加斯也是如此。查尔斯·索布拉吉还活着。
O’Coqueiro 的新主人在他被捕当晚吃晚饭的桌子上安装了 Sobhraj 的雕像。至于基兰·贝迪,她失去了工作——傲慢的受害者,当然,也是索布拉吉的受害者。这个坚强的女人在蛇的奉承的海啸下软化了。她非常相信他的康复,以至于她允许一个法国电影摄制组进入蒂哈尔记录它,给她的上司一个解雇她的借口。
与 Zende 所说的相反,我不相信 Sobhraj 对女人或金钱感兴趣。尽管他为了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展示了所有的金光闪闪,但他对生活的乐趣却给它们加了一层。他从来没有从那些出现在 Kanit House 然后死了的背包客那里得到超过几百美元的钱。每当他从交易中获得意外收获时,他就会立即飞往科孚岛或香港,并在赌场中将其全部吹走。他生命中的女人一直是犯罪企业或宣传的道具。如果查尔斯曾经是一个出色的种马,那么没人会这么说。他们会的。

2014 年 6 月 12 日,在巴克塔普尔地区法院举行听证会后,尼泊尔警方护送 Sobhraj。照片由法新社/普拉卡什·马蒂马/盖蒂图片社提供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比基尼杀戮事件。但在世界的那个地方,此类事件曾经被称为“amok”——一种“触发式暴行”,由马来亚的人类学家于 1800 年代后期首次观察到。现在,它们更多地发生在美国。埃里克·哈里斯 (Eric Harris) 和迪伦·克莱伯德 (Dylan Klebold) 在哥伦拜恩 (Columbine) 发疯。亚当·兰扎在康涅狄格州的纽敦肆无忌惮。曼谷的触发事件——我对此相当肯定——是 Ajay Chowdhury。这些谋杀案构成了索布拉吉丰富多彩的犯罪生涯中的一个非常简短的章节:一个以自我控制为荣的苗条、粗鲁的骗子的长期“过度杀伤”爆发。当乔杜里出现在画面中时,杀戮就开始了,当他离开时停止了。
令许多试图阻止它的人感到沮丧的是,Sobhraj 在我遇到他一年后被释放出狱。作为一名有犯罪记录的法国国民,他被匆忙赶出了印度。他定居在巴黎,据称他的人生故事获得了 500 万美元的报酬,并开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他最喜欢的咖啡馆接受一次流行音乐的采访,费用为 6,000 美元。
但这还远未结束。 2003 年,他出现在尼泊尔——世界上唯一一个他仍然是通缉犯的国家。 (泰国对包括谋杀在内的所有罪行都有诉讼时效。)他相信——至少是这么说的——对他不利的证据早已化为灰烬。我不太确定他相信这一点。他骑着摩托车在加德满都咆哮,就像他在果阿一样,让自己引人注目。尼泊尔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一辆租车的收据和在后备箱中发现的血迹证据,然后在赌场逮捕了他,这很合适。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刚刚看了一段 YouTube 视频,该视频显示 Sobhraj 因在加德满都被判谋杀罪而失去了最后的上诉。比基尼杀戮事件与现在相隔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他将结束的方式不再说明某些人将他们的病态鞭打到自焚的倾向。它所说明的是,在衰老过程面前,一切都是最终的徒劳。索布拉吉已经老了。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厌倦自己,他肯定变得愚蠢了。如果你和我一样长时间地看他的故事——无尽的恶作剧和混乱只会回到它开始的地方,一个牢房;钱被抢了,立刻赌了;跨越国家和大陆的无意义的永恒运动——你会看到 Sobhraj 总是很荒谬。我对他面对面的第一印象是咄咄逼人,无情的荒谬。
他的受害者是当时我同龄的人,毫无疑问,在我 20 多岁的时候带着同样的精神迷雾在地球上徘徊,在完全相同的年代。毫无疑问,这个故事很久以前就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我想知道,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是否也会被 Sobhraj 诱骗致死:在当时的照片中,他看起来像一个我会和他睡过的人。 70 年代——事实上,就像几个不同的人,我在 70 年代确实和他们一起睡觉。遇到他,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看起来不再像我曾经睡过的任何人,而且我事先知道他做了什么。像 Sobhraj 这样的罪犯现在是不可能的:国际刑警组织是电脑化的;一个人不能只用快速的谈话、性感的微笑和蹩脚的伪造护照就可以上下飞机和越境;世界上每家珠宝店都有监控摄像头,很快世界上的每条街道也会有。
但无论如何,我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象 Sobhraj 通过性魅力和卓越的狡猾将轻信的、不太聪明的投石者引诱到他的死亡网络中。但如果他杀的人并不比我更买他的行为,不管他当时有多迷人,甚至对他一无所知怎么办?如果他们看到的不是完美的形象,而是一个明显的亚洲人,滑稽的低俗失败者,就像在脱衣舞接头前穿着西装的庞斯,荒谬地假装是法国人,或荷兰人,或模糊的欧洲人,“比如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他可笑可悲但可能有用怎么办?大多数人不是被他的性感或油腻的口气所“吸引”,而是被廉价获得昂贵宝石的前景所“吸引”。很可能他的受害者认为他们在欺骗他,并认为他和我一样荒谬。或许他们相信——光荣地、开明的放纵——一个可笑的人也是一个无害的人。